第二章
大西洋岸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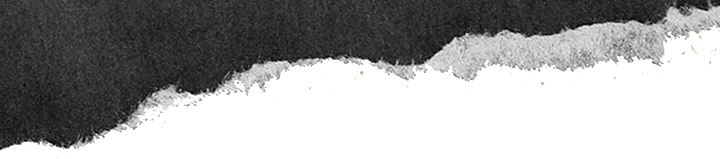
范绿妮心中生了一种急激的变化了,心头才定一定,不料旧墙上又见同一的文字出现。然而伊竟放大了胆,决定向自己前面可怕的径路上突进了。伊宛如见黑暗中放射着一条光线,顿时会悟了一件事情咧!
伊想到一个极简单的事实,这箭形是指示方向的,10的数字,是许多记号中的第十个。这些记号,挨着数目的次序,一定是从甲地引至乙地、丙地等用的。但是这些记号,可是一个人写的呢,还是许多人写的?这且不管,主要的问题,是范绿妮处女时代所用的姓名缩写,为什么理由,要出现在这惨剧的旋涡中呢?
其时罗法威村追上来的旅店马车,已经赶到这里,伊便乘了马车,命他缓缓的赴洛史卜邓去。恰巧到洛史卜邓,还在白昼咧!
马车徐徐行走,很为有益,为什么呢?伊在车上,中途又瞧见“11”和“12”的记号了。并且这两个都是在歧路的地方。这一夜在洛史卜邓宿一宵,明天早晨,再行出去探查。第十二号的记号,是写着在某处坟墓的墙上的。伊依着箭形的方向,走完孔卡诺街,还不见记号。暗想:“不要没有留心啊!”
这一天,差不多白赶了一天工夫,明天好容易发现了第十三号记号,字已几乎看不清楚。依着这箭的方向,向番史南进行,这里又迷了路。如此到罗发威村出发的第四天,伊到了大西洋海岸倍古梅尔海滨咧。在这村中宿了两夜,向村人们只是打听,也得不到什么眉目。
第三天早晨,由一半埋在沙内的岩石间走去,发现低崖上有一个小小的看守屋子,把两棵剥去皮的树木中间,胡乱砌了些墙壁造成的,像是税关上人用过的屋子。这屋子的门口,坚一块小形的太古纪念碑,说也奇怪,这纪念碑上,写着那“V.D’H.”三字,与“17”的号码。这里没有箭形,在那就有箭形的地方,画一大点,表示终止之意,就此完了。那看守小屋的内部,有敲破的瓶三个,空的食物罐三四个。
范绿妮暗想:“到底完了,一定有什么人在此吃过什么的,这大概是保存着的食物。”向对面一看,极近处有一个贝壳似的圆形小湾,这岩滨有一艘摩托船系着,在波浪中摇动又听得有村中来的男女二人,正谈着话,走向海滨去。不独听得声音,从范绿妮立的地方还很看得出姿态。一个中年男子,两手提着六袋食粮,跟在女的面后走来。
一会儿他把袋放在地上,说道:“奥诺梨奴,你这一次旅行如何?”
女的答道:“很好!”
男的又道:“你到底往哪里去的?”
女的说:“到巴黎去的,是主人的事。总算快了,到今天恰是一星期。”
男的道:“从旅行回来看看,究竟是自己的故乡好啊!”
女的忙应道:“自然如此。”
男的说:“你看,奥诺梨奴,你的摩托船,仍旧在老地方啊。我天天过来看的。遮着的防水布,还是今天早晨取去的咧。如何?这船仍旧很快么?”
女的点头说:“速力极快。”
男子道:“好得你又是一个会驾驶的人。你这么样的女子,能做这种粗事情,实在很奇怪。”
女子道:“这也是靠战争之福,我们岛上,年轻人都去打仗了,老人们捕捕鱼,近来是轮船也不往来咧!”
男子问道:“煤油够么?”
女子说:“加得很多,不打紧。”
男子说:“那么再会吧,奥诺梨奴,那袋由我袋在船中吧。”
女子摇头说:“不必!我自己来吧,你又很忙。”
男子道:“再会,奥诺梨奴,我去准备货物了。”
这中年男子,就此回村中去,忽又回头叫道:“你此去,当心着岛旁的暗礁,那边是著名的危险这处,名称就叫什么‘棺岛’,什么‘三十柩岛’,当真如此啊。奥诺梨奴,你留意些吧。”说完男子立刻被岩阴遮住不见。
范绿妮现在听了男子的话,突然一惊,“三十柩”,不是那可怕的画中文字么?
其时那女子将食粮袋正运入船中,瞧伊穿着白达牛特有的衣服,帽上袋着黑蝶形的缎带,范绿妮怎么不惊?心里叫道:“那帽子,不是十字架上三个女子戴着的么?”又见那女子年约四十光景,似乎很强壮,脸上被日光晒黑着,一双黑色的眼睛,更使伊脸部全体添上一种美丽来。天鹅绒的衣服,也很配身。
伊低声唱着歌,将袋运上船去,到一齐运完后,便看看天空,恰巧水平线上,布满的是黑云。然而这女子淡然的要解缆,歌更唱得响了。这是一种看守小儿的歌,伊张开口来露出洁白的牙齿唱着:
小弟弟,好孩子,快些睡;
笑而不哭快些睡。
小弟弟一哭,马利亚也要哭;
所以不要哭。
小弟弟,笑嘻嘻的唱着歌,
马利亚也微笑着。
合着可爱的小手,
向马利亚祈祷吧……
这女子歌还没有唱完,范绿妮已经立在伊旁边,低着头,脸色发青了。
那女子惊慌似的退后些,问道:“做什么?”
范绿妮颤声问道:“你现在所唱看守小儿的歌,是谁教你的?我的母亲,向来常唱这歌。母亲的故乡萨服亚地方,都唱这看守歌的。我自从母亲一死,就许久没有听得过这歌声了。”
这白达牛女子,呆呆的向范绿妮脸上默视着。正要启口说话时,范绿妮又反复问道:“谁教你的?”
这奥诺梨奴答道:“岛上的人教我的。”
范绿妮问道:“是棺岛么?”
伊回答说:“俗称棺岛,本来的名儿,叫作萨莱克岛。”于是二人互相对视了一下,在疑念之中,又含着一种想互相谈话、想互相谅解的心。并且伊们同时会悟双方没有恶意。
范绿妮忙道:“你且听着,实在很不可思议。”
奥诺梨奴点点头,大有很愿听的神气。
范绿妮便继续着说:“这事真是奇怪,不能明白,待我先来讲到这白达牛来的话吧。并且还有话要问你咧!”
于是,伊从当时偶然看影戏说起,见了自己的署名,便好奇心大发,到白达牛来了。后来在空屋中瞧见老人的尸体,就跟着这不可解的记号,来到倍古梅尔海滨。谁知这里也有记号发现的。
范绿妮大略说了一遍之后,奥诺梨奴很热心的问道:“这里也有你的署名么?在哪里?”
范绿妮说:“在那边小屋门口的石碑上啊。”
奥诺梨奴道:“我没有瞧见,写些什么?”
范绿妮说道:“是“V.D’H.”三字。
白达牛女子一听,脸上大为感动;,口中轻轻地念道:“范绿妮·岱爱投蒙。”
范绿妮大惊道:“你怎么会晓得我的姓名?”
奥诺梨奴握着范绿妮的两手,满面堆上笑来,同时眼中又含着泪珠,说道:“范绿妮姑娘,就是您么?真像做梦一般啊!这一定是圣母马利亚的指使,实在感激极了。”
范绿妮呆着,竟莫明其妙,忙道:“你知道我的姓名,知道我的来历么?请你快把哑谜儿一齐解释给我听啊。”
奥诺梨奴想了一想,好容易答道:“我实在无法说明,连我也不懂啊!但是我二人从此可以研究一下。你从火车上下来,先到的是什么村?”
范绿妮说:“是罗法威村。”
伊答道:“罗法威村,是我晓得的。那么那空屋的所在呢?”
范绿妮道:“离村一里半,是在入口的地方。”说完,又把小屋中发现的尸体,再详细把事实说了一下。
伊又问道:“那死人到底是什么人?警官验过尸么?”
范绿妮说:“没有,因为我带了村人再过去看时,尸体已经失去了。”
伊说:“尸体失去,是什么人藏匿着的么?”
范绿妮摇头说:“不晓得。”
奥诺梨奴道:“所以你一点也不明白缘故咧。”
范绿妮道:“实在不懂这缘故。不过我在小屋中,发现一张怪画。”说罢,又把磔刑的画,说明了一下,再说:“四个女子钉死在十字架上,想想也可怕啊!况且其中的一个,又是我自己,有我的姓名写着。此外三人,戴着与你一样的帽子。”
奥诺梨奴听了,又紧紧握着伊的手,说道:“怎么,四个女子,钉死在十字架上么?”
范绿妮点点头,又道:“三十柩,与你的岛,似乎有什么关系啊?”
奥诺梨奴突然用手按着范绿妮的口,说道:“低声,这种话不可说。此事的暗中,一定还有残酷的举动,你倘不当心,随便说说,万一被人听得,那就危险。你看见了那画中的事情,要严守秘密,将来自然会有知道的时候的。”
奥诺梨奴宛如暴风吹着树木,恐怖得乱抖。接着,又突然伏在岩上,两手掩面,祈祷起来了。
少停,才立起来说:“这事实在可怕,然而我们非尽自己的义务不可,万不能再在此踌躇了。”因又向范绿妮道:“你也一同去吧。”
范绿妮有些不愿意的样子,问道:“我到你岛上去么?”
奥诺梨奴还执着范绿妮的手,又问起话来。范绿妮觉得伊的声音很真挚,定是含有一种口中说不出的秘密。
奥诺梨奴问道:“你的姓名,当真是范绿妮·岱爱投蒙么?”
范绿妮点头称是,伊又问:“你父亲叫什么?”
范绿妮答道:“盎他·岱爱投蒙。”
伊说:“那么你是与一个自称波兰人的伏司克结婚的了。”
范绿妮道:“是的,他叫亚历西·伏司克。”
伊又道:“此人在结婚前,曾带了你逃走,因此与你父亲伤了感情咧!”
范绿妮称是,伊又说:“你是生过孩子的。”
范绿妮道:“不错,是男孩子,名叫法朗沙。”
伊道:“你可以说得没有看清楚儿子的面孔,为什么呢?这儿子一生出来,就被你父亲夺去咧!”
范绿妮又说:“是的。”
伊道:“你父亲抢了你的小儿,用自己的快艇,赶到外国去。这快艇在中途沉没了。从此以后,你就没有见过这二人。”
范绿妮说:“两个人都死了。”
伊问道:“你怎么晓得的?”
范绿妮道:“我托私家侦探与警察探查,那时他们问明四个没有溺死的水手,断定父亲与小孩子确已死了。”
伊道:“什么人会晓得水手们是谎话呢?”
范绿妮奇怪道:“什么谎话?水手们为何要说谎呢?”
伊说:“水手们,说不定他们不把证言卖钱,得了钱,什么谎话也肯说了。”
范绿妮道:“有谁去托他们呢?”
伊答道:“是你父亲啊!”
范绿妮道:“哪有这种事,父亲已经死了。”
奥诺梨奴便道:“那么我再来说一遍,你父亲确是已死,这句话,你怎么知道的?”
范绿妮一听,倒回答不出,便轻声道:“难道有什么缘故么?”
伊忙说:“且慢!船沉溺时,那未死的两个水手,你晓得姓名么?”
范绿妮道:“当时打听过的,现在忘了。”
伊道:“他们是白达牛人,都姓白莱冬,对不对?”
范绿妮说:“是的,是的。不过我……”
伊即道:“你虽现在初次到这白达牛来,你父亲从前为着著述上的事,曾屡次来过的。并且你父亲在你母亲活的时候,又时常住在这白达牛,因此与村人很熟。这么看来,那四个水手,是你父亲一向认得的。他们或者是为着交情,也许是得了金钱,说出这种谎话来那快艇虽是被风浪沉没,实则水手们将他们一老一小,送上意大利某港去了。大家都是会游泳的人,把快艇弄到洋面上去沉没也说不定啊。”
范绿妮很兴奋的叫道:“但是水手们活着,直接向他们一打听,也就明白了。”
伊答道:“四人之中,两个是在四五年前病故了。第三个叫马盖诺克,是个老人,至今很康健的,住在萨莱克岛上。第四个水手,你大概瞧见的,方才搬运食粮到这里来的啊,此人将所得的钱,做了资本,在倍古梅尔开着干货店咧!”
范绿妮道:“如此说来,只消一问他就明白,那么到干货店去吧!”
伊说:“不必如此,我比他晓得更详细啊。”
范绿妮听了,更觉奇怪,伊又说:“你别吃惊,我当真什么都晓得。你只管问我,我一句句都能回答你的。”
然而范绿妮此刻听了,虽像黑暗中见了晓光似的,可以打破这胸中的大疑问。但是竟没有询问的勇气,反觉得很怕打听事实咧。因叹道:“实在不明白,父亲为什么要如此?为什么要把自己与小孩子装作死掉呢?”
奥诺梨奴答道:“你父亲是立誓要复仇的。”
范绿妮道:“这是对伏司克,并非对我,我是父亲的女儿啊,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报复了。”
伊道:“你很爱你丈夫,你被他诱拐时,并不逃走,就此结婚的,这便是你公然的侮辱父亲了。所以这位倔强的父亲,他想定了念头,非实行不肯罢休。”
范绿妮道:“那么后来怎样?”
伊答道:“你父亲到底年纪老了,很爱孙儿,并且深悔当时不应该做这么一件过分的事,于是四面打听你的行踪,我也为着此事,曾到各处去旅行。沙德尔尼寺中也去过,恰巧你已出来,无从晓得行踪,大为失望。”
范绿妮道:“报上登一个广告,就好了啊!”
伊说:“你父亲曾登过一次很周密的广告,于是有人见了广告而来,你父亲去与他会面了。你道此人是谁?是伏司克啊!他也正在找你,爱着你,又恨着你。你父亲一吓,再也不敢登广告了。”
范绿妮默默听着,精神糊糊涂涂似的低头不语,歇了一下,才道:“照你说来,我父亲确是活着。”
伊道:“实在活着。”
范绿妮说:“那么你时常可以见我父亲么?”
伊点头说:“每天见的。”
范绿妮道:“这且等一下再谈。”又低声道:“关于小孩子的话,你怎么一句也不提,我很怕大约小儿已死,因此你不说什么了。”说罢,恐怖似的凝视着奥诺梨奴的脸。
奥诺梨奴笑道:“那可爱的法朗沙,要是死了,我怎么可以不说呢!”
范绿妮狂叫道:“那么,那孩子活着么?当真活着么?”
奥诺梨奴道:“当真活着,而且体格强健,举动活泼,真是一位很体面的公子了。我这抚育他的人,实在可以大大的夸口啊。”
范绿妮听到这里,两脚摇摇不定,双手撑住在奥诺梨奴肩头,哭起来了。一时悲喜交集,再也不能支持这剧烈的感动了。
奥诺梨道:“你且很畅快的哭一场吧,夫人!但是这事实在可喜,哭了之后,可以忘掉以前的苦痛咧。待我到村中旅店里去拿你的行李来。不打紧,大家都认识,肯给我的。”说罢,兴兴头头赶到村中去了。
过了三十分钟,回到海滨时,范绿妮用手招着,一壁喊道:“快些,快些!你在那里做什么?我赶紧要到岛上去啊。”
奥诺梨奴不答,徐徐走着,一笑也不笑。
范绿妮赶过去道:“你肯带我去么?我到岛上去,没有什么不好么?你做什么?神气有些不对啊。”
奥诺梨奴摇头道:“不然,不然,没有这种事。”
范绿妮道:“那么我们急急预备吧。”二人便一同将行李运上船去。
其时奥诺梨奴突然立在范绿妮面前,问道:“你所瞧见的那张可怕的画,画中处磔刑的女子,确是画的你么?”
范绿妮答道:“的的确确画的是我,并且还有我的名儿写着。”
奥诺梨奴道:“真是不可思议,而且令人胆战心惊。”
范绿妮摇头道:“没有什么,不知哪个晓得我姓名的人,故意恶作剧,胡乱写写罢了。我偶然想到从前的事情来咧。”
奥诺梨奴道:“不对,从前的事,且不去管他吧,我担心的,是将来。”
范绿妮忙问:“什么将来?”
奥诺梨奴道:“你且想想那可怕的预言啊!”
范绿妮道:“你也晓得预言么?”
奥诺梨奴道:“晓得的,所以一想到那画,更觉可怕咧!并且还有种种你所不晓得的恐怖。”
范绿妮笑问道:“什么事?你只是挂念着,因此你不愿意带我到岛上去么?”
奥诺梨奴答道:“你别笑,看了地狱中的火,谁能够笑呢!”说时,闭着眼晴,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,又道:“我自然是个愚笨的人,我是白达牛迷信极深的女子,什么鬼,什么怪火,我都相信着,实在迷信也不能一齐消灭干浄啊!你到了岛上,且去问问马盖诺克再说。”
范绿妮忙问:“谁叫马盖诺克?”
奥诺梨奴答道:“四个水手中的一个,是小官官法朗沙的旧朋友。此人抚养法朗沙,很费过一番力。他对于什么妖怪鬼神等事,那是比你那个有学问的父亲还明白数倍咧!并且最是不可思议的是……”
范绿妮忙问:“何事?”
奥诺梨奴道:“那马盖诺克,竟如有妖术一般,能知世人的命运祸福。”
范绿妮又问:“他怎样会晓得?”
奥诺梨奴道:“他自己对我说,曾把自己的手接触到神秘的中心了。”
范绿妮听得很为惊异,而且极愿听她的究竟。
奥诺梨奴道:“于是他被这火焰伤了手了,我亲眼瞧见过他的伤,恰巧像瘤那么样子,痛得异乎寻常。马盖诺克到底把一柄斧来,将自己的手斫去了。”
范绿妮大惊,因为想起罗法威村所见老人的尸体,是缺一只手的啊。于是问道:“去掉一只右手么?那马盖诺克斫断的,可是右手?”
奥诺梨奴答道:“确是右手,乃用斧来斫去,到今天已是第十天了,恰巧在我出门的前两天,他失去了手,我还替他穿衣服的咧!”
范绿妮发出干枯的声音来道:“那或者是的,我瞧见那空屋中老人的尸体,也缺一只右手啊。”
奥诺梨奴一听,吓得跳起来叫道:“哎哟!当真么?那定是马盖诺克了。此人垂着长发,须髯如扇形一般,如此说来,死者必然是马盖诺克呀!当真可怕极了。”
奥诺梨奴这么一说,顿时很留心似的向四面环视了一周,又画了一个十字,更轻声的说道:“马盖诺克还对我说过,他的生命,一定第一个失去。他与人类明白过去的事情一般,眼晴会透视到将来,人家看不见的,他都能明白。他又对我说:‘奥诺梨奴啊,我是抽到了一根不去的签,第一个牺牲者,是我。我一死之后,不到四五天,便轮着主人了。’”
范绿妮急忙低声问:“主人是谁?”
奥诺梨奴踏进一步,紧紧地握着拳头,答道:“是你父亲。我非防护他不可,非救助他不可,哪里可以使你父亲,做第二个牺牲者呢?现在赶紧去还来得及咧。我们万万不能踌躇了。”
范绿妮决然说:“我也一起去吧。”
奥诺梨奴哀求似的说道:“请你不用强迫,待我独自回到岛上,在日暮以前,必定可以把你父亲与你儿子,一起领到这里来了。”
范绿妮忙问什么缘故,奥诺梨奴道:“那岛上,在你父亲是很危险的,在你更为危险。你且想想四个十字架,十字架等候着的,那是那岛上啊。所以你一定不可往那种地方去,那边真是一个万恶的海岛。”
范绿妮问道:“我的孩子怎么样呢?”
奥诺梨奴道:“不满四五点钟,可以带到这里来了。”
范绿妮道:“还要四五点钟么?你怎么说出这些无情的话来。我在十四年极长的岁月中,只是为自己儿子悲痛着,此刻一听得他活在世上,怎么肯再守候四五点钟呢?我连一点钟也忍不住。与其在这种地方守候,我情愿忘命的过去冒险。别说一次,就是一千次也肯的。”
奥诺梨奴见伊决心非常坚固,晓得争也无益,便又画了一个十字形,祷告道:“上帝,请你作主吧。”
一会儿伊们俩已上了摩托船,奥诺梨奴就开了船,很巧妙的避着暗礁与沙滩,一路向前进行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