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
叛逆者之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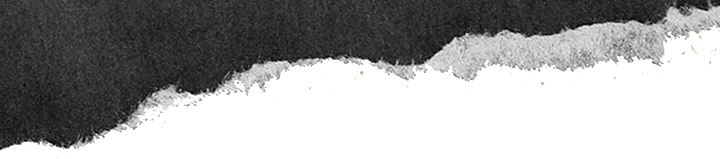
范绿妮坐在右舷,向奥诺梨奴笑着,这是一种含有不安的暧昧笑容,默默然宛如太阳光线射破暴风雨的黑云一般。其实确是幸福的微笑。伊的头发,虽偶然看得出有一二根白发,还是墨云似的结在颈边,脸色乃是南方女子特有的白色,眼睛碧澄澄地,如冬日的天空。身材瘦长,肩阔胸挺,声音似乎带几分男性的。谈到孩子,更为愉快,更为响亮。伊差不多除了孩子以外,不想说什么,也不想问什么了。
奥诺梨奴开口说道:“范绿妮姑娘,我所不明白的事,有两件:第一,是将你从罗法威引到此地来的目标,写这不可思议的记号的,到底是谁?定是有人从罗法威到萨莱克岛去的;还有一个疑问是,那老人马盖诺克,是怎样离开这岛的?是自己的意思要离开呢,还是被害后运过去的呢?”
范绿妮道:“这种事情,没有什么关系啊!”
奥诺梨奴道:“不然,此事极重大,我却因着去取食粮,常常用摩托船从岛上出来的。除我之外,就是二星期中,也决不会有一人到倍古梅尔或蓬拉佩去一趟的。岛上除了我的摩托船外,还有两只渔船。岛上的人卖鱼时,却是要往哇干奴方面去的。那马盖诺克怎么会到那种地方去呢?也说不定他是自杀啊!不过这么说来,那尸体何以会失掉?又是奇事了。”
范绿妮听着,就说:“这种话别说吧,无论如何,现在一到岛上,都可以明白。你还是多谈谈法朗沙的事吧。那孩子到岛上来的时候,是何种样子?”
奥诺梨奴答道:“法朗沙抱在马盖诺克手中到岛上来,乃是你父亲从你手中夺了法朗沙后,大约经过得不过四五天咧。马盖诺克依着你父亲的嘱托,只说是一位素不相识的贵妇人,把小孩子托付给他的。马盖诺克将法朗沙叫自己的女儿养育着。后来他女儿死了。从前我本来正在巴黎某氏家中充当女仆,那边出来了,回到岛上时,法朗沙已长得很大,只是在野中崖上,赶来赶去的游玩。恰巧那时节你父亲决定永远住在岛上了,我便受雇在他家中。到马盖诺克女儿一死,你父亲把法朗沙交托给我了。”
范绿妮道:“父亲曾把那孩子的名儿更换过么?”
奥诺梨奴道:“没有,主人在岛中,人家都称他盎他先生,小孩子也称法朗沙。他叫你的父亲,只是称着祖父亲,所以在岛上,人家也没有什么怪异。”
范绿妮又听了法朗沙性格的活泼、宽容,祖父亲非常爱他,面貌与自己相似,是个美少年,所以伊恨不得一刻也早一刻的去会见儿子。伊心中实在忍不住了,又晓得方才奥诺梨奴所唱看守小儿的歌,也是他祖父亲所唱,法朗沙时常学着的。因此,范绿妮不禁叫起儿子的名儿来道:“法朗沙啊,可爱的法朗沙啊!”
奥诺梨奴也说道:“法朗沙很忆念你。他常说:‘快些长大起来,把所读所写的功课做完了,自己要去寻访母亲咧!’”
范绿妮道:“你说的功课,是谁教他的呢?”
奥诺梨奴说:“起初是祖父亲教的。在二年前,来了一位家庭教师了,这是我在巴黎去请来,此人叫作史德法·麦路,是个很好的青年。他在战争时,因着名誉负伤退伍的,现在身体也强健了,曾经做过勇敢的事,得到许多勋章啊。”
范绿妮说:“那么这史德法·麦路,是家庭教师了?法朗沙此外每天与谁一起玩着?”
奥诺梨奴答道:“本来是与岛上孩子们玩着,后来那些小孩子,因为他们父亲出去打仗后,便由母亲领着,离开此岛咧。现在所剩的小孩子,只有三四人了,并且都是渔家之子此刻全岛的人口,也不过三十人光景啊。”
范绿妮道:“那是法朗沙没有朋友,很寂寞的。”
奥诺梨奴回答道:“但是有一个好伴侣,是马盖诺克送给他的一只犬,名叫惠儿,是泼特尔种与福克期德掠种的杂种,面孔很滑稽。这种聪明的犬,实在少有啊。”
范绿妮听了半晌关于自己儿子的话,一时悲喜交集,默然想着。不过渐渐的觉得沉郁起来,心底里涌上来的失望,足以压服表面的欢喜。伊追想着已往十四年间失去的种种幸福,一面又想到这长久岁月中盼望儿子的爱情,今天可以满足,倒又大为感动咧!
奥诺梨奴执着舵,很高兴的说:“路已过了一半,快到了。”
那时摩托船在古兰南群岛的视界内疾驶,右面远远瞧见喷马岬隐隐在水平线处。
范绿妮想着悲痛的往事,幼时死别的母亲,自己在刚愎的父亲手中成长大的儿童时代,变化极多的结婚时代。这样那样的想着,初次与伏司克会面,还只有十七岁咧!对这怪异不普通的男子,伊最初就发生一种恐怖。被他诱拐去的时候,实在恨极,暂时又幽闭过一下,日后想起了,也可怕啊!他用种种恶辣手段来恫吓,后来居然得到结婚的许可了。父亲既先行答应,叫伊也无可如何。
一回儿对于丈夫那种无检束的生活,也明白咧,他酷嗜酒和赌博,常常靠在他人的怀中,在那里玩着。他欺诈也来,恐吓也来,冷酷的地方,竟如发狂一般。做恶事差不多有一种天才。关于他一身的事,现在想起时也毛发悚然呢!
奥诺梨奴忽道:“范绿妮姑娘,你别这么只是乱想吧。”
范绿妮道:“我也并不是特地去想他,不过心里痛恨罢了!”
奥诺梨奴道:“自然自然,你已往的生活,已经完全牺牲掉了。”
范绿妮叹道:“这也是天罚。”
奥诺梨奴道:“然而已往之事,谈也无用了。现在等一刻儿你就要与父亲、儿子会面,幸福就在眼前,你把这些事想想吧。你看,那就是萨莱克岛。”
奥诺梨奴说完,便从座下取出一个大法螺来,学着古代船上的人一般,放在口边,用力一吹。那牡牛怒鸣似的声音,顿时散布海上了。
范绿妮很诧异的瞧着,奥诺梨奴道:“这就是送一个暗号给法朗沙。”
范绿妮说道:“怎么送暗号给他呢?”
奥诺梨奴徐徐答道:“我一向从他处回到岛上,一定要吹这法螺的。法朗沙一听得,便从崖径中赶来,到码头上候我了。”
范绿妮喜道:“那是一上岸,就会遇见这孩子了。”
奥诺梨奴答道:“就会瞧见的。今天我要使法朗沙吃惊一下咧!你且把面纱遮着双重,切不可将照片中看惯的面影给他瞧出来。我只算你是一位到岛上去游玩的妇人,与你闲谈着给他看吧。”
二人谈了一下,居然岛也看得很清楚,崖脚处被一群突出在海上的岩礁遮蔽着。
奥诺梨奴把发动机停止了,使用两柄桨,说道:“你看这里全是礁石,好像一群鱼类啊!海上虽没有风浪,前面也难行得很。”
这时候,只见打来的浪,几乎要撞碎那些礁石。回过来,又互相撞了几下,轰轰的响声和那雪白的飞沫,煞是可怕。摩托船摇动非常,宛如潜入瀑布之下了。
奥诺梨奴又说:“岛的周围各处,都是如此,不是小舟,就不能上岸。外面有大船来,万万不容易近。战争开始的二年前,来一个德国海军士官,值察过岛上情形的。因为不适宜于充潜艇的根据地,所以此次战争,德国的潜艇,从没出现过一次。总之是礁石守护着这岛啊。不过死伤人也很多的,你看那边瞧得见的大礁石处,真是极危险的所在,那许多礁石一一都有名称,或叫‘吃人’,或叫‘覆舟’,也俱有可怕的来历的。”
奥诺梨奴这么说完,恐怖似的指着那边竖起的礁石。只见那些礁石形状各各不同,也有像猛兽蹲踞之形,也有如圆柱直立之状,有的是尖刀山一般的三角形,有的是石屏风似的墙壁形,一个个可怕的形状,仿佛互相睨视着;并且个个是鲜血那么的红斑黑地花岗石。
奥诺梨奴又道:“讲这种话,我也很吓的。可是,那种大礁石共有三十个,都有些像动物的形态,所以有人称为‘三十野兽’。范绿妮姑娘,这不是可怕的事么?”
奥诺梨奴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,又低声的接下去说:“据你父亲说来,岛上渔夫们,把哀凯尤(礁石)一语和珊凯尤(柩)一语,拿来混乱着,所以本来称三十礁石岛的,后来无端的变成三十柩岛咧!范绿妮姑娘,要知道这些礁石,确是三十具柩。若是能够把这些礁石移去,那边一定可以瞧见有无数的骸骨充满着。主人常常说的,萨莱克岛的名称,是从‘萨尔夸法茄司’一语变化而成,也未可知。萨尔夸法茄司,乃一句古语,便是柩的意思。并且……”
奥诺梨奴说到这里,正要说下去,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了,指着礁石道:“你看,那右面大礁石的对面,不是有一个小小码头么?那边法朗沙戴着红帽子来迎接我了。”
范绿妮一听奥诺梨奴的话,极想早些看见自己的儿子,把身体靠在船边上凑出去望。
奥诺梨奴又道:“范绿妮姑娘,这萨莱克岛上太古墓标(古代岳尔人的墓标)极多,你父亲因为研究古碑很有益处,所以决定要永久住在萨莱克岛咧!这岛上的与别地方所有的太古墓标,也没有什么大大的差异,大半是同一形状;不过有一特征,说也奇怪,数目也是三十,恰与大礁石同数。并且与礁石一般,各有名称,如呼‘特尔哀洛克’、‘特尔凯里谦’等,不是极怪异的事么?”
奥诺梨奴只是很惊异的说着。原来这太古墓标,是古代岳尔人的墓标,石柱那么的两条粗石,上面载了巨大的扁平天然石,宛然是一只石桌子的形状。白达牛地方,也有许多留着。
一会儿那摩托船,到了大礁石旁,奥诺梨奴用桨一触礁石,绕将过去,便到码头了。
其时范绿妮大为失望,叫道:“呀!法朗沙不在啊。”
奥诺梨奴也叫道:“怎么法朗沙没有来?这是决不会的啊。”那边四五个低礁石并立着的地方,乃是码头,上面有三个妇人,一个少女,三四个老翁,立在那里等候摩托船过去但是不见有戴红帽子的少年。
奥诺梨奴轻轻说道:“什么缘故呢?我一吹法螺,法朗沙平日一定会到这里来接我的。今天怎么样了?”
范绿妮即道:“莫不是有病?”
奥诺梨奴摇头道:“不然,独有法朗沙,实在没有见他生过病。”
范绿妮也不解了,忙道:“那么,为什么缘故呢?”
奥诺梨奴道:“这个我倒也不明白了。”
范绿妮很恐怖的问道:“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么?”
范绿妮疑惑得甚么似的。这萨莱克岛,从地形说来,是细长的波状,地面到处生着参天大树。岛的周围,全由非常险的断崖包围着,海岸全是礁石。可以靠船的,只有一处,这就是此刻两个女子要把摩托船靠近的码头。这一部分,断崖略为开些,有四五所房屋建着,不过战争以来,也都成了空屋咧,风浪也是这一处好得多。
那边有两艘摩托船系着,二人上了岸,奥诺梨奴忙问小儿们道:“你们可曾看见我们家里的小孩子呢?”
一个妇人答道:“法朗沙正午时分在此地游玩着啊,但是他晓得你非到明天是不会回来的。”
奥诺梨奴道:“原来如此,我本来打算明天回来的,现在早了一天咧。不过法朗沙一定听得我的法螺声,为什么不出来候我呢?”
伊说罢,岛上的几个老人,要来帮伊搬运食粮袋。
奥诺梨奴止住他们道:“船中的东西,请你们不必去动它,我若在五点钟前不回到这里来,那么请你们把这些袋交与什么年轻人,替我送到泼洛里吧。”
一个男子就说:“我来送好了。”
奥诺梨奴道:“那么就托付与你,夸赖球,今天马盖诺克没来么?”
那人答道:“马盖诺克前几天赴蓬拉佩去后,还没回到岛上来。那时我送他到蓬拉佩去的。”
奥诺梨奴点头道:“如此么,夸赖球,他哪一日去的?”
夸赖球忙说:“好像是在你动身后的第二天。”
奥诺梨奴又问道:“他什么事要往蓬拉佩去呢?”
那夸赖球回答说:“据马盖诺克自己的话,也不明白他究竟往何处去。总之手上负伤很重,特地去祈祷的。”
奥诺梨奴道:“祈祷么,那是必然赴罗法威去了,那边有圣白尔蒲寺。”
夸赖球点头道:“对的对的,马盖诺克说过的,是圣白尔蒲寺。”
奥诺梨奴也不再问,马盖诺克的死,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了。当下伊就领了范绿妮,在岩石上凿开的路中,走将过去。
这路再穿过㭴木的树林,直到岛的南端。奥诺梨奴说:“总之我们非从岛上逃去不可,只消主人肯答应就好。主人听了我的话,或者说我迷信也论不定;然而主人自己,也有许多惊人的事实在手中啊。”
范绿妮即问道:“我父亲的住宅,离此很远么?”
奥诺梨奴道:“虽是地面连续着,其实是邻岛。由此地走去,要四十分钟光景。听说本来是倍纳祁克派修道院建的房屋。”
范绿妮道:“不过父亲并非独自一人居住,也不打紧啊,有法朗沙有麦路在一起。”
奥诺梨奴又道:“在战争之前,还有两个男仆咧!近来在旁边的,只有马盖诺克与我,此外有一个叫马利·罗岳夫的厨婢罢了。”
二人好容易走完了石崖,这里的路径,接近海岸,是花岗石质的凹凸径路,宛如波浪那么起伏着,所以行人必须忽上忽下。两旁都是枝叶茂盛的老树,太古时代这里所住的岳尔人,乃崇拜一种称为特累特教的顽固宗教,往往行活人祭的野蛮仪式,将活人放在祭坛前烧死,算是供献与神明的。
路径一入森林之中,那边各处就有青苔满着的石冢。这些冢上,都有一棵老树生着。前面是古时的石祭坛,还留着些痕迹,使人家追想那对于特累特大神的活祭,和信仰力的可怕咧!
奥诺梨奴再画一个十字,范绿妮跟着也画十字,身上不禁有些毛发悚然。
范绿妮道:“这真是一种阴森的地方,野花也不开一朵,岂不更觉得冷静寂寞啊?”
奥诺梨奴道:“草花一种上去发达得很奇怪,马盖诺克的住家,在里岛的一端,恰是仙女太古墓标的右面,那边草花极多,大家称他为花的卡尔伐利。”
范绿妮道:“很美丽么?”
奥诺梨奴道:“非常美丽。马盖诺克自己不知哪里去运了泥来,再混了些很可以充肥料的特别树叶在内,因此将草花种上去,竟有极好的花开出来。恐怕世界之上,再也找不到这种美丽的花了,实在是不可思议的花。”
二人绕着小山之下,路径便成斜下的坡子了。这溪谷就是与里岛相隔的境界,里岛面积虽很狭小,似乎来得高些。
奥诺梨奴指点着道:“前面就是里岛了。你父亲住宅的所在,叫作泼洛里。”
范绿妮看时,里岛也与前岛相同,四面由断崖包围着,有一条五十码光景的细长石崖,恰如一条天然的狭桥,乃是连结二岛的唯一地带。这顶上狭如斧斤一般,行人到底不能在上面渡过去,因此在略为离开些的地方,架着一顶木桥,借此往来行走的。
两个女子,两起的渡过此桥,桥身很狭,因着身体的重量与风力,那桥容易摇动,危险得很。过了桥,入里岛,先是一片原野枞树,都是梅花形的种着;另外有一条路,是分向右面去,走入竹林中去的。
奥诺梨奴忽然对着竹林中一望,叫道:“史德法先生!”
范绿妮便问伊道:“你唤谁?就是那史德法·麦路么?”
奥诺梨奴答道:“不错,他是法朗沙的家庭教师啊!我瞧见他慌慌张张,赶往桥那边去的。史德法先生为什么不答应我呢?你没有瞧见那边一个人影么?”
范绿妮答道:“我倒没有留心啊。”
奥诺梨奴道:“戴白帽子的一定是史德法先生,我们且看着桥的一面,他总要过桥的。”
范绿妮道:“这去管他做什么?我们不是打算急急赶去么?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出来,那还了得!”
奥诺梨奴也道:“不错,那么快些走吧。”
二人又急急行走,心中不知不觉的骚乱起来,自然脚步加速。脚步一加速,恐怖更为增加。岛的形渐渐狭小,走到了泼洛里境界的低墙处,忽然听得家中一阵剧烈的叫声。
奥诺梨奴侧耳一听,说道:“你听得这声音么?是女子叫声,那厨婢马利·罗岳夫啊。”
奥诺梨奴赶到门旁,急忙用钥匙开门,但是过分慌张,竟不容易开。伊就说:“不行,我们从竹篱的破隙处进去吧。你随我来,向右走。”
二人便跌也似的由篱隙走入草原,在一条被青苔和野藤埋没着的路上赶去。
奥诺梨奴故意在外面叫道:“来了,我们回来了。”其时屋内叫声顿止。
奥诺梨奴又说:“什么事呢?不好了,马利·罗岳夫很可怜的……”伊说着,又紧紧拉住范绿妮的臂,说道:“我们绕到后面去吧。前面向来下锁的,窗上有铁梗插着,恐怕无效。”说时,范绿妮触在树根上,跌了一交。爬起来时,奥诺梨奴已绕往后面,瞧不见了。
范绿妮独自赶到门口,连连叩门,但是门不开,屋内又有人的叫声了,这是男子之声,而且是听惯的父亲之声。
范绿妮退后数步,抬头望望楼上,见上面突然开了一扇窗,父亲探出头来,脸上现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,尽力大叫道:“救命!快些!畜生!救命啊!”
范绿妮也发着绝望之声,叫道:“父亲,父亲!”
那时爱投蒙氏虽曾把头向下面一望,可并没瞧见自己女儿,于是急急想逃到露台上去,不料背后枪声一响,窗上玻璃都碎了,他一面高声呼“杀人啊”一面又回到室中。
范绿妮十分恐怖,发狂似的向四面环视一周,怎么样可以救父亲的命呢?墙壁又太高,要上去时,没有接脚的地方。忽见二十码光景的对面壁上,有一架梯子,伊便放出混身的力量来,去运这重大的梯子,拿来靠在窗下。
可是在这生死存亡大悲剧的一瞬间,人类的头脑,往往有不可思议的活动。范绿妮现在不免要疑到奥诺梨奴为什么没有声音呢?为什么只是踌躇着呢?
这梯子达不到窗口,但是范绿妮已上了梯了,好容易伸手触到了露台下面的横木处,室内还在那里格斗,杂乱的声音中,还时时混着爱投蒙的叫声,伊才得抬着头瞧见室内的格斗了。
这时候爱投蒙再退到窗边,两手无力下垂,身体动也不动的立在那里,是一种无决断的模样,眼中发出异样的光来,似乎等候着什么可怕的事,口中吃吃的叫道:“杀人!杀人!是你么!畜生!法朗沙!法朗沙!”
范绿妮心想:“爱投蒙可是要叫孙儿来杀他么?难道是法朗沙也陷入危险么?也许是负了伤死去了么?”
范绿妮用尽全身之力,好容易爬到横木之上。伊打算忘命的叫道:“父亲,我来了。”但是这声音已在喉咙中消灭完了,一看伊父亲的前面,只离开五步处,有一个少年,拿着手枪,向父亲瞄着。但是这少年是戴红帽子,穿铜纽扣的法兰绒衬衫的。他那脸上,恶狠狠的牵动着,与伏司克狂暴的本性发作时那种表情无异。少年那边瞧不见范绿妮的身体,他那充血的眼晴,只是集中在敌人身上,打算立刻开枪;特地延长时间,徐徐施行这凶暴的行为。
范绿妮糊糊涂涂更从横木上爬起来,要赶进窗中去,已经来不及了。枪已开放,爱投蒙顿时一声悲鸣,倒在楼板上了。
这一瞬之间,后面的门忽开,奥诺梨奴已赶将进来,一见这惨状,就惊叫道:“法朗沙,你你你。”伊一壁叫,一壁拦住少年退路。少年又举起枪来,再放一枪,奥诺梨奴顿时倒在门旁。少年由伊身上跳过去逃走,奥诺梨奴还叫道:“法朗沙,法朗沙,这不是梦么?这是真的么?法朗沙。”
那时室外一阵笑声,原来是少年在那里笑着。
范绿妮听了这恶魔似的笑声,便觉得与伏司克是丝毫不错的。爱投蒙横在地板上,那快要断气的声音中,微微呼着自己女儿的名道:“范绿妮……范绿妮……”他还把一双极钝的眼睛,对女儿看看,又尽力呼道:“范绿妮……恕我……范绿妮……”
伊流着泪,一面在父亲额上接吻道:“父亲,您认得出我么?”
爱投蒙嘴唇动着,似乎想说什么话,但是声音模糊,已不成言语。范绿妮忙把耳朵凑在他口上,也听不出。他的生命已如退潮那么渐见微弱,精神已陷入朦胧的状态。
范绿妮凑在他唇边再听时,他父亲用了最后的气力说道:“当心……当心……神石……”他这么断断续续的发音,又突然抬起半身来,眼中宛如灯火似的,最后一亮。
范绿妮见了父亲这种表情,晓得危险也逼到伊自己身上来了。父亲又发声道:“快些逃……离开此岛……要遇害的……快些,快些……”这声音很哑,并且含着恐怖,但是极清楚。接着把头突然垂了下去,后来说些什么,很难明白。
范绿妮所听得出的,只有“十字架……萨莱克的四个十字架……我女儿……我女儿……磔刑……”这一点儿罢了。
这时四面极静,范绿妮似觉有重物压在胸头,这重量一刻一刻在那里加倍,只听得有人说道:“你快依你父亲的话,早早逃开这岛去才是。”发声的乃是奥诺梨奴。伊脸色苍白,两手把一团手巾按住伤口,那白色手巾,已被流出来的血染红了。
范绿妮道:“话虽如此,现在非先救护你不可呀。这伤怎么办才好呢?”
奥诺梨奴道:“我是不妨的,现在就会有人来了。可恨啊,只消我早了一步进来,便决不致演成这种惨祸,那楼下的门,用钉钉着啊。”
范绿妮急道:“你非先把伤处治疗不可,且好好躺着吧。”
奥诺梨奴道:“我倒不妨,那厨婢马利·罗岳夫,倒在楼梯上,负伤极重,恐怕不能救也论不定,快些去看一看吧。”
范绿妮就从方才法朗沙逃出去的门中,走到广阔的楼梯处,一看那马利·罗岳夫,真只有一丝呼吸了,差不多范绿妮过去时,伊恰在同时断气。这厨婢竟做了这不可思议悲剧中的第三牺牲者咧!那爱投蒙氏是第二牺牲者,马盖诺克的话果然中了。


